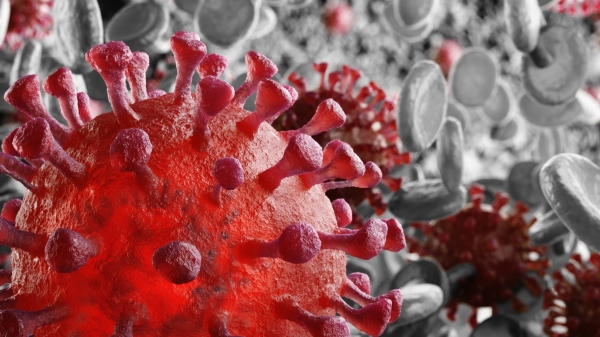
请叫它“中共病毒”。希望人们能永远记得,为着“圣王的面子”而失去生命的人们,以及“儒官集团”(包含 WHO 在内)在其中扮演的共犯角色。(图片来源:Adobe Stock)
【看中国2020年2月24日讯】有许多人对“中共肺炎”这一名词很不满意,坚持要将病毒“去中国化”,坚持只能说“新型冠状病毒”。
黄智贤说:“不要用中国的城市名字命名疾病或病毒,这是歧视。”
WHO 声色严厉地说:新发现的病毒,名称绝对不可以叫“中共病毒”。
当台湾的“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”决定继续采取通行的“中共肺炎”简称,天朝媒体立即发动攻势,痛斥“以疫谋‘独’尽曝,冷血自私狭隘”、“借机吃人血馒头”、“台当局借疫生事其心可诛”。
只是,许多人都指出了:那么,“非洲猪瘟”如何?“西班牙流感”如何?“日本脑炎”如何?“德国麻疹”如何?“斯德哥尔摩症候群”如何?“伊波拉病毒”如何?乃至,“香港脚”如何?
喜欢用军机、航母与核导弹来宣扬“华夏式人道主义”的“儒官集团”,会去使唤 WHO,来全面取缔“中共病毒”这个语词,这个会将“儒教圣王专政优越论”钉在人类法庭的耻辱柱上的语词,应该是没有人会意外的事情吧?
但“儒官集团”的“正名术”,并无法真正否定一个现实情景:不少疾病的命名,都以各自的方式,携带着关于特定历史脉络的记忆,例如西班牙流感和伊波拉病毒。这些疫病的名字,都登录着一个“历史现场”。
执是之故,在这篇文章,以及之后的文章,我会继续使用“中共肺炎”这个语词,但不是基于天朝主义者所谓的“歧视”,而是缘于:希望人们能永远地记得,为着“圣王的面子”而失去生命的人们,以及“儒官集团”(包含 WHO 在内)在其中扮演的共犯角色。
“种族歧视”?
仔细观察这次天朝权力集团为中共病毒的“正名作业”而做出的部署,不能不说精密。同时,更重要的是,还能让我们看到,西方“文化左派”著名的“政治正确”话语,是如何与帝国儒教的“道德正确”话术交织出密切的“共谋关系”。
在天朝权力集团宣布武汉封城后,伴随着 WHO 对中国防疫工作不断高唱赞歌,各国开始纷纷以怀疑的眼光,注视着在中国发生的疫情,也陆续展开各种 WHO 所不乐见的紧急疫病风险管理措施。
在这个氛围中,中国各地的使馆,也逐渐相应地加大外宣作业的脚步。其中的重点,除了要求批判中国防疫处置的欧洲媒体对天朝权力集团道歉,就是去宣传“中共肺炎的名称是种族歧视”,并且将“中共肺炎”的命名,与各国对中国的旅游限制挂钩起来,声称这些都是“反华的西方帝国主义”的表现。
众所周知,今日的 WHO,乃是“全球儒官社会”的领头羊,天朝权力集团最忠诚的国际随附组织。在这波天朝权力集团的“大外宣”中,WHO 当然是不会缺席的。
WHO全球传染病预防部门负责人布里安(Sylvie Briand)公开表示,使用中共肺炎这样的命名,就像是“中东呼吸症候群冠状病毒”或“西班牙流感”这样的名称,是需要避免的,理由是“会造成地区与族群的污名化”。
WHO公共卫生紧急计划执行主任莱恩(Michael Ryan),也同样主张,人人都有责任确保疾病的命名不会造成污名,而且,“根据种族来进行描述是完全不可接受的”。
“谁”歧视着“谁”?
时间来到2月7日,WHO 就正式在官方记者会上宣布:为这避免污名化武汉市,正谨慎替病毒决定正式命名,预计未来几天将公布最终的官方名称。WHO新兴传染病部门负责人范柯霍夫(Maria Van Kerkhove)说:“我确定你们都看到许多媒体仍用武汉或中国来形容(病毒),我们想确保不要有污名。”
事实上,WHO 之前为这次检出的病毒做出的“暂定官方命名”,一直是“2019新型冠状病毒”(2019-nCoV),从未涉及疫情发源地中国武汉。西方媒体注意到,WHO 在给予新型冠状病毒正式名称上,显现“前所未有的谨慎”。
隔天,2月8日,中国国务院就随即召开记者会,由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言人宋树立出面,宣布“2019新型冠状病毒”所引起的肺炎病症,暂时统称为“新型冠状病毒肺炎”(英文名称为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),简称“新冠肺炎”或“NCP”。
网络上随即出现讥讽的声音,说 NCP 是“New China Pneumonia”(新中国肺炎);天朝权力集团是站起来了,但中国人民却倒下了。
无论如何,至此为止,天朝权力集团的努力显然成效无多,各国媒体似乎依然普遍采用“中共肺炎”的通行命名。
于是,到2月12日,WHO 再度出马,秘书长谭德塞(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)亲自告诉记者:“我们如今已有此一疾病的名称,那就是COVID-19。”WHO 对中共肺炎给予了“正式命名”—— COVID-19,至于病毒的名称,则由“国际病毒分类委员会”命名为 SARS-CoV-2。
他还明确表示,选择这个名称是为“避免指涉特定地理位置、动物物种和人群,符合国际为避免污名化所做的建议”。
随后,台湾的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发布声明,为与WHO公布的国际资讯接轨,并使民众方便理解,由新型冠状病毒(2019-nCoV)所引起的肺炎正式称呼为“COVID-19”,而简称为“中共肺炎”。
天朝媒体接着就咆哮了:“中共肺炎是种族歧视!”
不过,真的要谈“种族歧视”吗?
我曾经在国外多年,我的亲身经验,让我明白西方社会确实存在着对“华人”的仇视或歧视,但也同样确定,西方社会内在的民主伦理和人权观念,会时刻制约着这些倾向。
反而是在汉字文化群内,“小粉红”高亢的“反西方文化帝国主义”口号,会不断附着在“反种族歧视”的“政治正确”上,来掩护自身的“中华型帝国主义”思维。而““华夏式的人道主义”话术,显得像是一条隐蔽的通道,让“中华型帝国主义”,可以经由西方“文化多元主义”的“政治正确”,从从后面偷溜进来,乃至进而大大方方地将自身表象为不可逾越的“道德正确”。
进一步说,在人们的直观中,其实许多人都了解:在汉字文化群,取缔“中共病毒”这个名字的做法,其实不过是老儒教“正名论”的反复再生产,不过是借由规范语词的使用来维护“君父权威的威信”的儒教统治术。
就此来说,取缔“中共肺炎”这个命名的“正名术”,其所意图的政治效果,就与央视说赖清德“窜访”美国一模一样,不多也不少;总而言之,就是要为“中华型帝国主义”赋予某种原本并不存在的“道德重量”。
“文化左派”的“政治正确”
在WHO 将中共肺炎“正名”为“COVID-19”后,台湾的天朝主义文人,也开始引经据典,说明这个命名的“正确性”,驳斥“台湾媒体配合中共规定,不称中共肺炎,只说新冠肺炎”的批评,认为这些批评纯然是“假新闻操作”。
台湾的天朝主义文人,如我预期的,开始拿 WHO 与天朝权力集团的说法来说嘴,主张全面取缔“中共病毒”这个语汇,并且自认这是“杜绝种族歧视”的“政治正确”,绝对不能质疑。
按照天朝主义文人的说法,在公卫与医疗社会学文献中,对“疾病命名”造成特定人群或地方污名的反思,早已获致定论,于是,WHO 才会在2015年发布“Best Practices for Naming New Human Infectious Diseases”(“命名新人类感染疾病的最佳实务准则”),建议不该使用人名、地名、职业、动物、食物、文化、族群、产业来命名新疾病,要必须以受到疾病影响的系统、严重性、症状、病原体等为准。
天朝主义文人没说的是:这份建议性的“实务准则”,在发表的时候,就被医疗界批评过度“政治正确”;“文化左派”不切实际的“实务准则”,不但容易导致重复的疾病名称,而且不够明确,一般人无法快速了解一个名字所指的疾病究竟为何,徒增一线医疗作业的困扰。对这些医疗界人士,反而是“文化左派”诟病的命名方式,才能登录一种疫病发生的“历史现场”,才透显了“医疗人文主义”的本色。
天朝主义文人另一个避讳的地方,是不愿意去说明:这次中共肺炎的命名,其实乃是这个所谓“实务准则”自身的首度实作;将中共肺炎命名为 COVID-19,是 WHO 第一次运用这份“实务准则”。
COVID-19变成“人类头号公敌”
最后,天朝主义文人没有提及的另一个事情是:当WHO秘书长谭德塞宣布中共肺炎的“官方正式名称”COVID-19,他同时也宣布了—— COVID-19 是人类的“头号公敌”,要求各国“尽量积极地”对抗这项疾病。
谭德塞表示:“如果世界不想醒来,将此病毒视为头号公敌,我不认为我们能够汲取教训。…我们必须采取一切行动,使用可取得的武器”。”
从“中共肺炎”到“COVID-19”,这个来自中国的新疫病,瞬间变脸为人类必须采用“一切可能手段”来加以“围堵”的“头号公敌”。这番“头号公敌论”,当然“自然正当”地证成了天朝权力集团以“战时状态”的名义而采取的“军管”隔离措施。既然是“人类头号公敌”,采取任何手段,即便是高度违反国际人权规范的“例外手段”,也是合乎“正义”的“伟大事业”。
就这样,一个依照“文化左派”的“政治正确”而命名的病毒,反而顺利地启动了一场对“人类公敌”的“战争状态”。
有趣的是,也在这个时候,人们才发觉,在“钻石公主号”上的日本检疫官,由于完全遵照WHO之前刻意淡化疫情严重性的作业指示,没有穿上全套防护装备就进行检疫工作,也感染了中共肺炎。
回到那个记者会上,谭德塞却正高呼:“我们仍处于围堵策略,我们不应允许此一病毒有地区性传播的空间。”他急促呼吁:“我们必须利用当前的机会窗口强力反击,在各个角落团结对抗此一病毒,否则我们可能会有远多于目前的病例,付出远高于目前的代价。”
面对一向要求各国不得对中国采取旅游和贸易限制措施的WHO,美国的防疫专家摇摇头,叹息现在才想要围堵病毒传播,恐怕为时已晚。(待续)
(本文为《上报》独家授权《看中国》,请勿任意转载、抄袭。原文连结)
